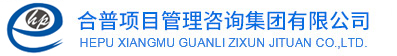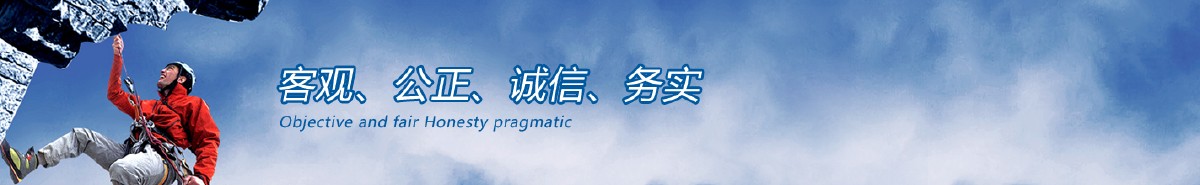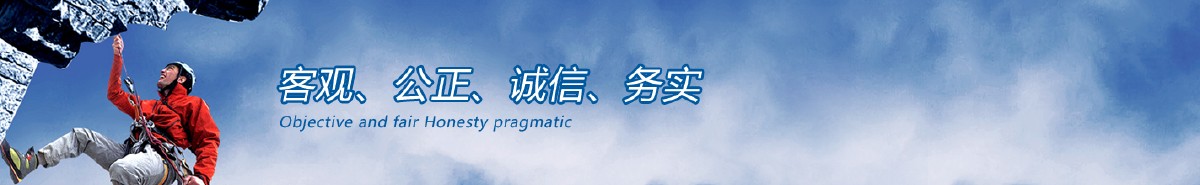01
框架协议招标、集中采购等首获官方认可
《指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同类型、重复性招标项目,招标人可以结合项目实际,采用框架协议招标、集中招标等方式实施”。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框架协议招标”这一采购组织形式,尽管实践中央国企采购对框架协议、集中采购等模式早已运用成熟,但由于《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并未提及此类模式,导致相关实践操作长期处于制度依据支撑不足的状态。《指引》的出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标志着框架协议招标从实践做法上升为官方认可的采购形式,为招标采购活动充分发挥规模化、集约化效益提供保障。
02
明确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
围绕保证金管理,《指引》第十五条明确将串通投标、文件异常一致、资质造假等异常情形列为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具体情形,将以往实践中有所争议、常常需要诉诸法律还难以解决的问题予以明确。这充分体现民商事行为中“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精神,不仅为招标人处理异常投标情形、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依据,也通过经济手段增强了对围标串标等不良行为的违法成本和震慑力。当然,招标文件和保函格式中仍然需要列明上述情形的后果,以便招标人无争议地主张合法权益。
03
招标信息公开制度化
《指引》第十六条要求招标人按月度、季度或年度周期发布招标计划,这是提升招标透明度的重要创新。这一规定表明招标信息公开正在从单个项目公告向系统性、前瞻性信息披露转变,充分体现了国家鼓励信息公开、推动阳光采购的坚定决心。这有利于改变以往投标信息被动获取的局面,特别有利于中小企业和新入市主体提前调配资源深入用户沟通交流、做好投标准备。从深层次看,这项规定将推动招标采购主动寻找供应商,扩大供应商寻源范围,减少单一来源采购,避免因投标人不足导致的招标失败,促进形成更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生态。
04
推广电子评标,驱动评标模式变革
《指引》第二十三条要求招标人代表应“熟练运用电子评标工具”。这一规定蕴含评标模式变革的深意,表明国家鼓励评标朝着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电子评标将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提高评审客观性和工作效率。随着智能辅助评标、远程异地评标等模式的推广,评标工作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型,这对招标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员、评审专家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
05
明确评标报告可复核纠正的情形
《指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招标人在公示中标候选人前应对评标报告进行审查,并对六类具体情形可要求评标委员会复核纠正。该条款针对评标标准执行不严、评分畸高畸低、异常报价分析缺失等常见问题,明确了复核纠正程序。这一设计既尊重评标委员会的独立评审权,又建立了必要的制衡机制,实质上强化了招标人对定标结果的主体责任。招标人不再被动接受评标结果,而是负起责任主动介入,形成评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闭环,有助于提升评审工作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06
引入后评价制度,推动管理持续改进
《指引》第三十七条引入招标后评价制度,要求定标后30日内对招标全过程进行科学性、合理性评估。这一规定将项目管理中的“后评价”理念引入招标领域,推动招标管理从“一事一议”向“持续改进”转变。为推动后评价制度平稳有效落地,建议招标单位采取"由点及面、分步实施"的推进策略。初期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项目作为试点,如对投资规模较大、技术复杂度较高或存在异议或投诉的等关注度较强的项目,集中资源开展深度评估。通过从重点项目入手,招标人可以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快速积累经验、完善机制,为后续全面推行奠定坚实基础。随着实践深入,后评价将从单一的项目复盘工具,逐步发展成为组织知识管理和招标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最终实现招标质量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
当然,还有其它的创新点,如招标人要打造专业化的招标队伍,内部要设管理机构,建立决策、合规、监督等管理机制,评标时得考虑项目全寿命周期的综合成本;招标资料的保存责任在招标人,至少存 15 年,定标全程都要记录,变更超过中标金额10% 的得全面审核,对供应商也要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国有企业还得向国资委报告招标主体责任履行情况等等。
随着《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招标投标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于招标人而言,指引既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指南,也划定了责任红线;对于投标人而言,指引的实施将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随着指引于2026年正式落地,招标投标领域将迎来新一轮提质增效的改革浪潮,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